周末早起,推开窗,阳光很淡。翻出硬盘里一堆老片子,看见《东京物语》的文件名,突然想起第一次看它是大学时代的事了。那时候我二十出头,在学校的放映厅,觉得这片子太慢、太平淡,甚至有点闷。如今快四十岁了,父母也到了片中老人的年纪,再打开这部电影,眼泪就那么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。
那些被忽略的细节,现在全看懂了
《东京物语》(1953,小津安二郎)讲的是一对老夫妻从尾道坐火车到东京看望子女,却发现孩子们都很忙,只有过世儿子的媳妇纪子愿意陪伴他们的故事。情节简单到几乎不像是电影,更像是生活本身在缓缓流淌。
第一次看的时候,我觉得这些儿女也没做错什么啊,大家都要工作、要生活,老人来了安排住宿、送去热海度假,该做的都做了。但这次看,我看见的全是那些没说出口的失望:老父亲在诊所外等了很久,儿子医生匆匆出来说”抱歉太忙了”;母亲想和女儿多聊聊,女儿却一直在张罗美容院的事;孩子们凑钱把父母送去热海,以为这是孝顺,却不知道老人在那个嘈杂的温泉旅馆一夜未眠。
最让我心碎的是老母亲回到尾道后那句:”我们在东京待得挺愉快的。”她笑着说,眼神却空落落的。我突然想起过年回家,妈妈总说”你回来就好,不用买东西”,但我知道她盼了很久。我们都在说谎,父母假装不需要陪伴,我们假装已经尽力了。
纪子这个角色,二十年后才看懂她的选择
年轻时看这片子,我最不理解纪子。她丈夫都去世八年了,公婆劝她改嫁,她为什么还要守着这段过去?现在再看,我明白了——她留住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那种被需要、被记得的感觉。
纪子陪老人坐电车、带他们游东京、耐心听他们讲话,这些都是亲生儿女做不到的。她对老母亲说:”我其实很自私,因为想到他,所以才对您这么好。”这句话以前听不懂,现在懂了。有些情感需要载体,有些陪伴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活着、还爱着。
老母亲临终前把自己的手表送给纪子,那个镜头小津用了很长的静止画面。两个女人没有太多对话,但那种传承的温柔、那种”你比我的孩子更懂我”的默契,全在沉默里了。我看到那里,想起外婆去世前拉着我的手,什么也没说,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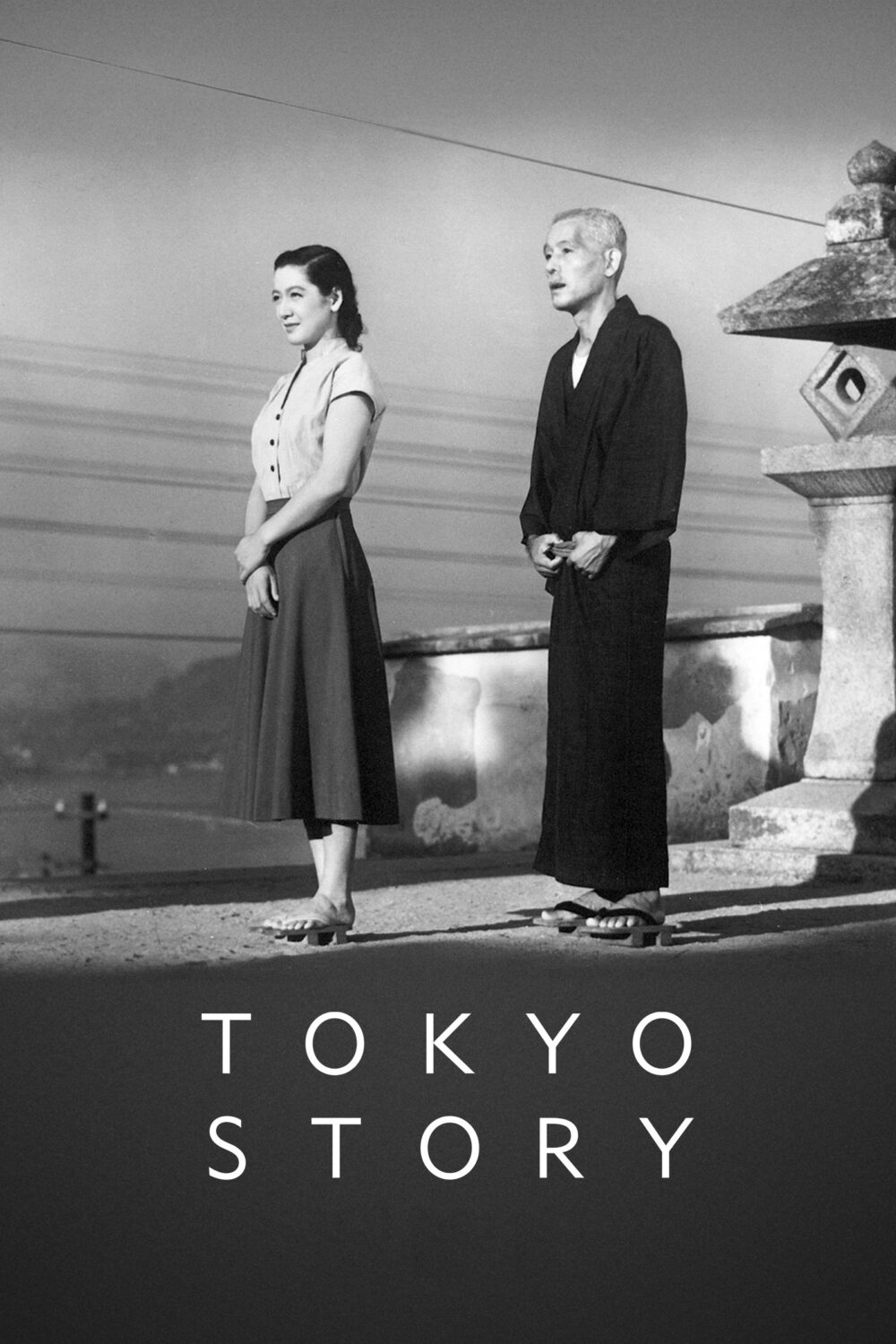
小津的固定机位,现在看来是种体谅
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有个特点:摄影机总是放得很低,像是坐在榻榻米上看人。以前我觉得这是形式主义,现在觉得这是他对普通人最大的尊重——他不俯瞰、不评判,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,看着生活发生。
那些长镜头、固定机位、空镜头,年轻时看觉得沉闷,现在看反而觉得克制。电影里有很多屋檐、走廊、火车站台的空镜,没有人,只有风吹过、云飘过。这些画面给了观众喘息的时间,也给了片中人物消化情绪的空间。
老母亲去世后,老父亲一个人坐在房间里,镜头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。没有特写、没有配乐,只有时钟的滴答声。那种孤独,不用任何技巧就能传达出来。我想起爸爸一个人在家的样子,他总说”我挺好的”,但那个背影明明很落寞。
关于错过,没有人是故意的
这部电影最残忍的地方在于:没有一个人是坏人,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儿女们不是不孝顺,只是真的很忙;父母不是不理解,只是希望被看见。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但错过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电影结尾,老父亲对纪子说:”人生真是令人失望啊。”这话说得太轻了,轻得像叹气,但重量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他不是在责怪谁,只是陈述一个事实: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,但其实离别每天都在发生。
我关掉视频,给妈妈打了个电话。她接起来的第一句话是:”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”我说没事,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她沉默了一下,然后笑着说:”那你多说会儿。”
我们聊了很久,聊她最近种的花、楼下新开的超市、邻居家的猫。那些琐碎的、日常的、以前我会觉得无聊的话题,这次我听得很认真。挂电话前她说:”有空就回来吧,妈妈做你爱吃的。”我说好,这次是真的想回去。
《东京物语》没有给答案,它只是告诉你:来得及的时候,请多陪陪他们。因为等你懂得这部电影的时候,可能已经晚了。







